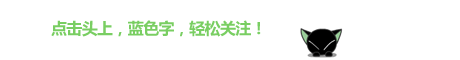
北京的深秋,叶蓓发了新专辑。
发布会那天,高晓松、老狼、朴树、郑钧、张亚东、小柯都来了,叶蓓和他们站在一起,仿佛回到白衣飘飘的校园民谣时代。
新专辑名叫《流浪途中爱上你》,“消失”了9年后,这是叶蓓给自己的音乐礼物,她包办了词曲,讲自己的故事,亲人、朋友以及世界。
演出很暖,台下坐满人,老狼和许巍分别跟叶蓓唱了新歌,唱到《青春无悔》的时候,台下有人哭了。
歌声就像咒语,打开时间的宝盒,尘封已久的过往都跑了出来。
那回不去的青春,若说无悔,又仿佛有憾。
1994哪一年,大学刚毕业,我买了一张CD《校园民谣1》。
当时,这张唱片在市场上一碟难求,人们都是冲着老狼的《同桌的你》去的。
其实,我更喜欢专辑中另外一首老狼的歌——《流浪歌手的情人》,也是高晓松的词曲。
中学时代,我们是看着三毛长大的,当然,中间还夹杂着琼瑶“作作作”的爱情,和金庸的黄蓉郭靖小龙女杨过。
《橄榄树》是当时最火爆的歌曲,我们小时候家长没有钱,也没有时间,每周上6天班,更没有休假这个说法。
直到18岁,我只和妈妈去过一次千岛湖,还有一次普陀山,这是我少年时光的全部旅行经历。
寸步难行的我们,更加向往文艺作品里的“流浪”。
现在想想,当时“流浪”的概念,和现在“旅行”其实是一回事,只不过,没钱没目的没攻略,听起来更加颓废浪漫。
我们那时的青春其实很励志,所以不需要太多鸡汤,那种颓废,才更加吸引人。
上了大学,做一个流浪歌手的情人,更是颓废浪漫鄙视链的顶端。
虽然我的学校是一个学经济学贸易学外语,很现实功利的地方,但是,浪漫还是90年代初校园的主旋律。
我的宿舍在4楼,有个男生追求我的同学,一到晚上11点快熄灯时,总抱着吉他在窗下,一首一首弹唱这自己写的歌曲,直到我们都能一字不差的唱出他的歌。
学校里最受追捧的男神,也都是乐队里的歌手。
我的一个师哥,是我当时男朋友的铁哥们,和高晓松一起玩过青铜器乐队。因为崇拜罗大佑(大右),所以师哥给自己取艺名叫“小左”。
每次他一拿着吉他上台演出,唱崔健的《花房姑娘》,唱罗大佑的《鹿港小镇》,学校里一定是万人空舍,无数女生为之癫狂迷醉。
而能够捕获男神的心灵,有资格做流浪歌手女友的,一定是校花或者系花,不仅美艳动人,而且聪慧绝伦,写得一手好文章。
我的两个师姐,就这样做了男神歌手们的女朋友。我也总是边仰视边靠近她们,混迹在学校的文艺和文学圈。
流浪歌手和他们的情人,在学校里行走,都是自带光环的。校园里流传着他们的故事,直到故事变成传奇。
那些当年的文艺女青年,后来怎么样了?
要么像周迅或张曼玉,恋爱到老,文艺到老,但是,更多的是,适应了现实社会,老大嫁做商人妇。
理想的爱情一个个破碎,就好像光辉璀璨却又短暂即逝的烟花,师姐们甩了流浪歌手,有了更靠谱更体面的男朋友。
“小左”南下打工,历经艰辛,后来回南京自己创业,白手起家,几起几落,现在已经是当地著名的民营企业家,妻子朴素贤惠,儿女听话乖巧。
高晓松也功成名就,只不过还没离开文艺圈,算是守得初心。只不过往往不是女人甩他,而是他甩女人。
“伤害”这个词,在青春里可以算是一个褒义词。
就像是练吉他,指头上的划痕,就像是极限运动,身上的伤疤,是一种可以引以为豪的资本。
如果一点都没受过伤害,这样的青春一定很苍白,很贫瘠。
就像40岁的高晓松说:
“年轻的时候每件事你都想明白,每个人你都想仔细想把他看透。每个事情你想明白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,甚至这个社会,这个时代,你都特别想去明白。但是你其实明白不了,你连你自己最爱的人坐对面你可能都不能全明白。可是年轻的时候就太想明白,因为老觉得有一些事情不明白就是生活的慌张,后来等老了才发现,那慌张就是青春,你不慌张了青春就没了。”
1999年,叶蓓出了张《纯真年代》。
同名主打歌是郁冬写的,他的《露天电影院》一歌我也很喜欢。
想起了纯真的年代,
你给我最初的伤害,
还有那让我忧愁的男孩
别问我爱会不会老
这些事有谁会知道……
在这之前,有一部大导演马丁·斯科塞斯拍的非著名电影,也叫《纯真的年代》。我看了很多遍,讲的是克制的爱情,守住了承诺和责任,却对真爱终身抱憾。
纯真,讲的是一种真诚,不带世俗功利、发自内心的情感。只是,这种纯真,很短暂,很脆弱,就像爱情一样短暂,就像青春一样脆弱。
高晓松还说过:“很多人分不清理想和欲望,理想就是当你想它时,你是快乐的。欲望就是当你想它时,你是痛苦的。”
我们亲手把纯真埋葬,用物质和体面建造我们生活的殿堂。
我们用从容取代慌张,付出的代价是,从此失去勇气和激情。
而多年以后,再次听到校园民谣时,我们会落下眼泪——
当年的自己,是那么的不顾一切……
只是,这眼泪,是快乐的眼泪。
更多文章,请长按二维码关注花生地
生活是一座好玩的大花园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