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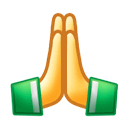
2
“青春若有张不老的脸——”爱上你是最快乐的事。
“天黑黑,欲落雨”
“听,海哭的声音,叹息着谁又被伤了心,却还不清醒,写封信给我,就当最后约定——”
(再后来有天,他短信我说,今儿被人嘲讽了、怎么净听这么老的歌。
我莞尔。回复道:那是因为,有些【新】歌、连变老的机会、都没有。)
音乐的美好质地,与文学一样,与绘画一样。
至坚至善的,都禁得住,时光冲洗、人世变迁、高墙阻隔。几百万流量,不算什么;百年之后,千年之后,尚有人在听、在读、在看;听到读到看到那一声那一行那一笔,少年清泪,漫漫共婵娟。千载厚的光阴,霎那化为薄薄米纸、可一吻而透。是 为贵重。



